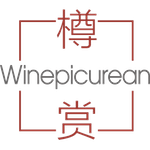很多年前,吕杨还是上海半岛酒店的侍酒师,还是小清新麻杆身材的时候说过,“如果我送客人一杯甜酒,大家都很喜欢,可是没有人会点一瓶甜酒。”
后来不止一位五星级酒店的侍酒师说过类似的话,相信到现在甜酒的销售也没什么起色。

肥鹅肝传统上是苏玳的绝配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喝甜酒变成没有品味的事了?“不懂葡萄酒的人才喜欢喝甜的,懂酒的都喜欢干的,甚至越干越好。”香槟产区的低Dosage甚至零添糖风潮,还有澳大利亚克莱尔谷追求的bone dry雷司令,多少都因为这种心理。德国和阿尔萨斯那些off dry或者semi-sweet的雷司令,就被一脸嫌弃。因为没看清楚酒标买到甜雷司令的消费者像踩到雷一样惊叫一声,只恨开了瓶不能退货了。
勇于承认自己喜欢甜酒的人两极分化。要么是无知者无畏的葡萄酒小白——我有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最近移民加拿大了,我很为她高兴,从此可以天天喝加拿大冰酒了;要么是特立独行的葡萄酒人,比如唯一常驻中国的葡萄酒大师赵凤仪,常常说她最喜爱的葡萄品种是麝香Muscat——就是酿造Moscato d’Asti的品种,在她获得葡萄酒大师的头衔后也未改口,这让她显得很酷。
一般人对于甜酒的印象大概是被大量廉价酒带坏的,那些最最简单小甜水似的Moscato d’Asti 、Prosecco、新老世界都有的桃红和雷司令。可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一些酒也是甜的,比如年份波特(Vintage Port)、阿玛罗尼(Amarone)、苏玳(Sauternes),仍然是老派葡萄酒鉴赏家的心头好。

一个法国企业家说,他只喝甜感几乎消失的老年份伊甘。
无处不在的营养专家又要跳出来说了:摄取过多糖分对身体不好,现代人不喝甜酒是因为健康意识提升了。喝一杯甜葡萄酒相当于吃一块蛋糕?我怎么没看见蛋糕行业衰落啊。
对于甜酒的偏见甚至在专业人士中也占主流。有一年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赛在意大利举行,赛后安排几百位评委参观Prosecco产区,说他们有一块天价地Valdobbiadene。我听了很震惊,反而没记住价格。晚上吃饭,毫无悬念搭配的全部是Prosecco,十几二十瓶摆在桌上随便喝。一个法国评委老男人先是抓紧桌布嚎叫一声,“我能不能也喝点红的!”然后拿起一瓶酒标上有Valdobbiadene字样的酒嫌恶地说,“用这么贵的地做甜酒是图啥。”
当然有残糖的酒和真正的甜酒是两回事。比如纳帕一个成功的酒庄庄主承认,她的干红葡萄酒总有6-8克残糖,这也是法律规定干型葡萄酒残糖的上限。虽然酿酒师想酿得更干,但美国消费者喜欢有点甜。
除了屈从于喝惯了可乐的消费者的口味,对于香槟和雷司令这样高酸的葡萄酒,如果葡萄本身的成熟度一般,酸度单薄尖利,残糖总能使酒更圆润和平衡。我喝过特别干涩严肃的香槟和雷司令,一点都不愉快,可以想见酿酒师也是个天赋一般还很拧巴的人。

有无花果点缀的冷鹅肝更是甜酒绝配。
至于德国和阿尔萨斯那些顶级雷司令,当华美多汁的酸度与慷慨的甜度融合在一起,口感饱满奢华,余韵悠长摇曳,犹如一首咏叹调,谁还在意里面到底有多少克糖呢?
甜酒的极致在于酸与甜的完美平衡。一瓶顶级雷司令或苏玳甜酒的糖度总是远远高于你的想象,因为有绝佳的酸度辉映。因为缺乏酸度而平庸的甜酒难免沉重疲乏,像演奏了一半就跑调了的乐器。
有关于复兴甜酒的种种努力总是有点徒劳可笑,即使是地位高高高在上的伊甘酒庄Chateau d’Yquem也不能免俗。我参加过两次全程用珍贵的伊甘甜酒配餐的晚宴,一方面感觉真奢华,一方面感觉好辛苦,甜上加甜让味蕾迅速疲倦,菜和酒都失了色。

年份波特搭配蓝纹奶酪和甜点皆好。
我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观点,甜酒的衰落源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化和平民化。在一个王室成员在大街上穿仔裤骑单车被赞赏的时代,要求吃饭前来一杯苏玳当开胃酒,或者上奶酪和甜点的时候搭配一杯托卡伊或者波特,显得多么落伍与不合时宜。

有些朋友的出生年份,在波尔多很差劲,在波特却不错。
然而法国人说了,“去年的夏天在伊甘的酒瓶中燃烧”,甜酒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,生活黯淡之处一点幽微的光亮。在盛夏的花园里打开一瓶冰凉的Moscato d’Asti或者甜美的桃红;在漫长的法式晚宴的尾声,倒上一杯琥珀色的陈年托卡伊或者苏玳;在有人过生日的时候送上一瓶和水果挞绝配的意大利甜酒Vin Santo 甚至朋友年份的波特……生活总不会太糟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