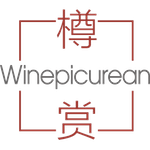今年早些时候去法国香槟产区,见到酒农香槟大神Anselme Selosse。这些年Selosse香槟价格飞涨,还常常一瓶难求。其他小农香槟就算挂上“Selosse弟子”之名,酒都好卖得多。

Selosse率先使用,又放弃了生物动力法。
“我已经放弃生物动力法了。”Selosse语出惊人,脸上挂着他常有的迷之微笑。
放眼葡萄酒世界,也许只有他有资格这么说,在很多酒农还在生物动力法的迷雾中求索,求之不得、辗转反侧的时候,他似乎再一次走在了前面。
在葡萄酒爱好者中间,也许只有wine geek才会试图厘清有机酒、生物动力法酒和自然酒之间的关系和差别,也未见得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酒瓶上那些认证标签多付银子,除非酒真的好。

新西兰中奥塔哥,生物动力法酿酒师手中的土壤。
新西兰中奥塔哥是一个有机酒和生物动力法酒比例很高的产区,Mt Difficulty酒庄的销售总监Fraser Mackenzie分析,为什么有机酒不像有机苹果那么打动消费者,“因为葡萄酿成酒,有一个转化的过程,感觉有机不有机就不那么重要了。”
就更不要说一般消费者都不知道在干嘛的生物动力法酒和自然酒了。

Blair Walter, Felton Road酒庄,庄主示范如何使用配方肥料。
同在中奥塔哥产区的Thomson酒庄有一位生物动力法专家Su Hoskin,给我们演示了按照生物动力法创始人,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人Rudolf Steiner的500-507配方制作的肥料,比如500是把牛粪装入牛角中埋进土里发酵,隔年春天再挖出来,把这样100克东东加入旧橡木桶中先顺时针再逆时针搅拌出漩涡,洒到1公顷葡萄园中就能起效——是不是难以置信?
配方还使用春日菊、荨麻、橡木皮、蒲公英、柳条、矽石等材料,“这就像我们人生病了要喝草药茶一样,”Su Hoskin穿着大地色系的棉麻衫裙,没有化妆,说话又柔和又坚定,特别令人信服。

Su Hoskin就像一位生物动力法代言人。
所有生物动力法酒农都在自家葡萄园里堆肥和做“草药茶”,共同点是只要你感兴趣,就会啪一声跪在地上,掀开木板捧出一个陶罐,抓一把给你闻,“不臭吧?” 神奇的是真的不臭,这些黑黢黢的肥料湿润、新鲜、生动,带着泥土的清新气息。
生物动力法要求按照生物动力法日历安排农事,依据月亮进入星座的时间,分为花日、果日、叶日和根日,根日适合翻土,果日适合采收。要避免在满月时剪枝,以免损耗葡萄树的元气。事实上1988年就实行生物动力法并且当时被视为异端的 Lalou Bize-Leroy女士根本反对给葡萄剪枝,她认为葡萄树能感知疼痛,而她能感知葡萄树在哭泣。因为葡萄藤恣意生长,在种植密度高达1公顷1万株的勃艮第葡萄园,到后来,人要走进去作业都困难。
2008年,在审慎观察和实验了20年之后,Aubert de Villaine将罗曼尼康帝酒庄全面转向生物动力法。

Leroy女士和de Villaine先生性格似乎截然相反。
虽然前有疯狂感性的Leroy女士,后有严谨理性的de Villaine先生,生物动力法至今仍是少数人的游戏。中文世界最好的葡萄酒作家林裕森说,波尔多很多酒庄在实验了生物动力法之后认为效果不好,纷纷放弃了。至今只有Latour、Pontet Canet等少数酒庄坚持并获得成功。林裕森的看法是,“生物动力法需要一个行家,但是波尔多的体系是各自为政。葡萄园经理收到通知说不能用农药,他当然觉得效果不好。”
所以不管知不知道生物动力法这回事,资深的葡萄酒爱好者一定有意无意喝到过伟大的生物动力法酒。因为像Latour、Pontet Canet这样的酒庄,无须用生物动力法作招牌或行销。林裕森指出,实施生物动力法后,Pontet Canet这几年的酒风是有变化的。好想做个垂直品鉴,印证他的说法有没有!

Latour和Pontet Canet这样的酒庄不需要贴“生物动力法”标签。
但自然酒就不是人人都喝过,偶尔喝过的人可能还有一种“自然酒就是臭酒、缺陷酒”的坏印象。用有机或生物动力法种植酿造,极少干预,不加硫的自然酒,常常有氧化、高挥发酸、马厩气息等等问题。除了对自然酒深有情结的少数人士,别说葡萄酒爱好者了,专业人士也大喊吃不消。但林裕森说,他也喝过很多纯净透明的自然酒,自然酒还在发展中,不能以固有的刻板印象判断。
总之不管是生物动力法还是自然酒,在酿酒高手手里才能运用自如。Selosse虽然声称放弃生物动力法了,但承认看月相和跟随直觉酿酒,所以他放弃的,只是生物动力法那些繁琐而不明所以的规条。蠢人亦步亦趋,聪明人为我所用。Selosse的酒中充满仿佛从大地深处萃取的强大能量,已经足以说明一切。